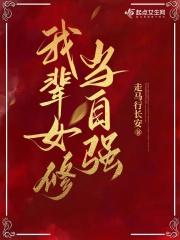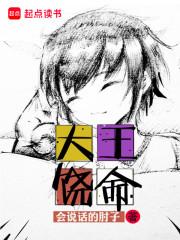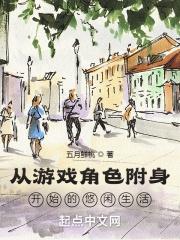第1494章 南事(上)
新粮刚刚入仓,村头的大槐树下,一片欢声笑语。
一河之隔的对岸,草市已经开张了,男男女女聚在一起,人声鼎沸,十分热闹。
一队披发骑士牵着马路过,好奇地看着这一切。
葱、韭、葵、豆,草鞋、蓑衣、篮子、簸箕等,各色商品都有,实在太丰富了。
要知道,这可是乡间草市啊,连地名都没几个人知晓,就有这么多待售货物,和南安郡县里的集市也差不多了。
带队的姚苌也很吃惊。
一路行来,还是第一个碰到的乡间草市呢,货品如此之多,让人不得不遐想建邺的坊市有多么富庶。
就在此时,前方行来一支车队,草市上的小商贩和农人们立刻抱怨不休。
“这些伧子,就知道抢我们的生计,实在过分。”有商贩说道,声音还不小,很快引起了共鸣。
“江南就没人吃盐酪。怕是放到化成灰,都没人买吧。”另一个商贩说道。
“这两年来了很多北人。”一个中年男子叹了口气,说道。
他脚下躺着几只鸡,脚缠在一起,扑腾个不停,一时间羽毛飞舞,鸡屎遍地。
“确实来了很多北人。”不知道谁附和了一句,顿时大伙都不做声了,继而眉头也皱了起来。
说痛恨吧,谈不上。不过那些人的嘴脸是挺难看的。小门小户还好,世家大族可就飞扬跋扈了,争水、争地毫不手软,你就是打官司都打不过他们,无他,上头有人。
之前那个唐剑无条件偏袒北人,张硕也不是什么好货,借着整顿军务的由头,不知道办了多少扬州土豪,更兼在淮南大开杀戒,远近震怖。
但说到底,倒霉的不是他们平头百姓,只是看在同为吴人的份上,有些兔死狐悲之感罢了。
说不痛恨吧,看看他们做的这些事,以及至今还在一批批南渡的伧子,子孙的生计怕是会艰难许多,少不得要开荒了。
总之他们的到来不是好事,很让人反感。
但他们死又死不掉,就连集结起来南征的大军也多为荆州人,你说说看,这都什么事?
“去岁陈麦,价钱好说……”商贩们正哀叹间,新来的车队已经摆开了场子,开始叫卖了。
“新制盐酪,府中用不完,便拿来发卖。双钱易一块,廉甚……”
“修剪出来的枯柴,都来看看……”
前面一个人说完,后面一人又喊道:“若有人想佣作的,速来,以五十人为限。”
“佣力自给,天经地义。开挖沟渠,人来即可。”
“可有会木工的……”
车队众人嗓门大,虽然口音怪异,但不至于听不懂,一时间吸引了很多人过去问询。
姚苌牵马从旁边路过,暗道这定是某个庄园把用不掉的东西拿到市面上售卖了。
这种事情很常见,无论南北方都有。因为急着处理,价钱很不错,往往能吸引众人购买,但对于拿着自家鸡鸭果蔬出来售卖的本地农人来说,可就不一定是好事了。
若想把手头的粮食、家禽、果蔬之类的物品卖出去,不降价是不可能的,这就不就亏了么?
农人攒点东西出来卖都是有原因的,一般是想贴补家用,比如换购农具铁器等。可被这么一搅和,唉,啥也别提了!
马儿打了个响鼻。姚苌收回目光,又扫了下队伍。
百余名南安羌人骑兵披头散发,定定地看着琳琅满目的货物,十分出神。
姚苌皱了皱眉,唤来几名亲随,让其下去约束部伍,别弄出什么劫掠之事出来。
他今年才十五岁,在家中本来就不是特别受重视,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历练之机,可别搞砸了!机会就这么一次,过了就没有了。
亲随们的约束还是有效果的,骑士们纷纷收回目光,继续赶路。
就这样一直走到入夜时分,他们终于抵达了石头城,稍事休整几天后,便将跟随第三批南下的队伍前往广州。
姚苌听到时有些惊讶,道:“竟已走了两批人?”
“那还有假?”新任扬州都督靳准幕府的漕运令史斜睨了他一眼,说道:“都已经渡过去万余人了。”
“渡至广州?”姚苌暗恼这小官也敢给自己脸色,不过还是和颜悦色地发问。
“不是广州是哪?”小官不满道:“你们的马怎么回事?没装粪兜?”
说完,他指着地上的一滩马粪,怒道:“自己收拾干净了,若让参军看到,你们完了。”
姚苌怒气在蓄积中,眼睛都眯了起来。
不料小官十分强硬,见状冷笑道:“怎么?要发作?想想招讨使是谁。”
姚苌神色一凛,冷静了下来。
招讨使自然是正在南阳、襄阳一带度田的太子了。他若在此闹事,一定会传到太子耳朵里,那样就麻烦了。别说功劳,能不被追究责任就已经万幸。
于是他换了一副笑脸,道:“官人且放心,我这便让人清理。”
呃,也别怪小官如此,关键在于姚苌根本不是官,也未穿官服。他和他手下这百余人,理论上来说就是“乡勇”,虽然他们打仗的经验很丰富。
小官见他服软了,点了点头,道:“广州世兵说不定都已在开往交趾了,你们若拖拖拉拉,南下得太晚,到时候吃亏的可是你们自己。”
说完,一振衣袖,走了。
姚苌暗骂一声,芝麻大的官也这般趾高气昂,你可知我是何人?
这个时候,他暗暗着恼,征南结束后一定要弄个官当当,不然真是走到哪里都被人轻视。
林邑啊林邑,希望你们坚持得久一点,别让人一下子就打趴下了。
清理完马粪后,姚苌又让人去领取米面,埋锅造饭。
夜晚的石头城静谧无比,江面上渔船星星点点,漂移不定。偶尔有一两艘船只靠岸,上来的也是风尘仆仆的旅人。
他们大包小包,行色匆匆。姚苌甚至不用问,只从外表上一看,就知道是南渡定居的北方人了。
太子不断度田,被迫远走他乡的人太多了。丹阳虽然已经有点人满为患的意思,但依然是很多北方人心目中最佳的南渡目的地。
当然,来了后他们可能会后悔的,进而继续迁徙到其他地方,但这都是后面的事了。
******
九月二十日,最后一批船队在清脆的钟声中离开了石头城,顺江而下,直抵大海。
靳准亲来江浦码头送行,随后便沉默不语。
事实上,别看船运得这么繁忙,但还有很多兵士走的是陆路,却不知有没有到达广州了。
不过无所谓了。
他本以为自己会是南征统帅的——即副招讨使,事实上的统帅——结果天子更青睐交州刺史孙和。
既如此,那就算了吧。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即可,无需关心太多。
林邑国的情况,最近他也有所了解。
看似人多势众,其实不怎么堪战。与交州土兵厮杀,胜负就在两可之间,撑死了林邑稍占上风罢了。
南征的主力是荆州世兵。
最初由刘弘创建,陶侃、诸葛恢继之,鼎盛时至五万众,传闻战力颇为强劲。靳准本不信,但来这边后检阅了两次部队,教练监(此职已由巨鹿郡王邵慎接任)出身的他一眼就看出,这些部队底子都很不错,也难怪当年陶士衡有信心与大梁王师厮杀呢。
这样的部队即便投降后战斗力不及当年,对付小小的林邑国还不手到擒来?
靳准的心思甚至已经放到了地方的治理以及家族的经营上面。
扬州现在真有些乱,来的人太多了,没有人造反,但地方治安恶化得很厉害。作为都督,他有义务协助刺史处理这些事情。
另者,因为调走了大量水陆兵马,他得防着天师道徒死灰复燃,再度作乱,虽然他们已经被狠狠打击过很多次了。
至于家族么——他已经决定从介休老宅迁一部分子弟过来了。
以前小看扬州了,这地方固然湿热,但物产真的丰富。只要占上一块好地,用心经营,很快就能积累起大量的财富。
君不见,就连远在辽东的燕王以及豪商巨贾糜氏都来建邺做买卖?
靳氏的财富还是太少了。
今上在位时,或还能维持富贵。今上不在,太子继位,多半就要没落了。
而天子年岁渐长,气力渐衰,去年洛阳西苑讲武,他就没再带着亲军奔马驰射,还能活多久是个问题。
时间不多了。
天子派他来扬州坐镇,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有些事情,心知肚明即可,无需宣之于口。
靳准倒背着双手站在江风中,苍白的胡须随风摆舞。
江面之上,百舸争流,一往无前。
江水之畔,百姓围观,热闹无比。
这个天下,已然形成了自己的规制,无论是战争、治理还是别的什么,无需外人过多干涉。
它会自己运行,并且有稳固的内生力量,推动着它向前行走。
当然,也不是没有问题。
以长江为界,南北两侧的内生力量是完全不同的。将来怎么办,谁都不知道。
但人力有时穷,什么事都要天子一人做完,又置后人于何地?
靳准离开了江浦,准备回去写奏疏。